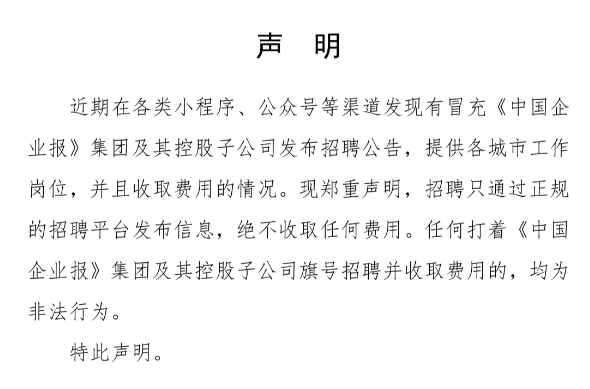风沙是戈壁滩的主人,中铁电化运管人是它掌心里一株倔强的胡杨。沙,这无休无止的侵略者,日夜啃噬着沉默的线路,将它们埋进黄褐色里。沙害,是悬在铁路脖颈上的一根看不见的绞索。

戈壁的清晨,空气里还凝着昨夜的寒气,风刀子似的,刮过裸露的皮肤,留下粗粝的痕迹。没人喊疼,疼在这里是寻常事,像呼吸一样自然。青年员工冲在最前面,他们的脸还带着些未褪尽的稚气,却已学着扛起铁锹,走向那无边无际的黄沙战场。他们有的刚从书本里爬出来,有的已让戈壁的风沙在指缝间刻下了年轮,此刻却都只有一个念想:把沙子从钢轨上铲走。

铁锹扬起又落下,铲起沉重的沙,也铲起沉重的喘息。汗水很快浸透了那层薄薄的工装,紧贴在年轻的脊背上。天闷得像个烧透了的铁罐子。太阳悬在头顶,无情地烘烤着这片没有遮拦的土地,汗水流进眼睛,涩得发疼。空气在视野里扭曲、晃动。就在这滚烫的煎熬里,忽然,几点冰凉的东西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是雨。稀疏的雨点,小得可怜,带着天空遥远的气息,砸在滚烫的沙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只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像细小的叹息。几点雨滴落在滚烫的脖颈上、额头上,那一点突如其来的冰凉,像是给烧红的烙铁淬了一下火,激得人猛地一哆嗦。

这点小雨,是杯水车薪,连尘土都压不住。但它带来的那丝转瞬即逝的凉意,却像沙漠旅人喉咙里滑过的一滴水,是绝望里生出的幻觉般的甘甜。空气里那股能把人烤焦的热浪,似乎被这几点微弱的凉意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青年们没有欢呼,只是动作似乎轻快了一点点,铲沙的节奏里,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生气。汗水依旧在淌,但皮肤上那灼人的痛感,暂时退却了一点点。这点凉爽是短暂的,如同戈壁里一切珍贵的东西,但它来过,身体记住了那片刻的喘息。

活儿干得久了,有人摸索出了门道。不再是一窝蜂地乱铲,分成了几拨。一拨人专对付轨道上的积沙,铁锹贴着冰冷的钢轨,像外科医生剥离坏死的组织;另一拨人仔细检查清理过的轨道,用刷子甚至手指,抠出藏在缝隙里的沙砾,像清理伤口的腐肉。
不知过了多久,站内股道终于重见天日。原本被沙子掩埋的轨道恢复了清晰的轮廓,变得干净整洁。清理沙害保护了线路设备,延长了其使用寿命,降低了后续的维护成本。清理后的轨道,像一条被洗净的脊梁,重新挺直在戈壁苍茫的背景里。列车可以从这干净的脊梁上安全地滑过去了,载着货物,也载着远方模糊的念想。

风沙依旧在远处呜咽,像不甘心的野兽。那点小雨早就没了痕迹,连地面都干了,仿佛从未降临。只有皮肤上残留的一丝记忆,证明那片刻的凉爽并非幻觉。青年们抹了把脸,汗水混着沙土,成了泥。戈壁的太阳依旧高悬,烘烤着这片沉默的土地和他们同样沉默的脊梁。日子就是这样,在风沙和铁轨之间,在酷热和那点微弱的凉爽之间,那点凉意,或许会像一粒沙子,嵌进某个年轻人在某个疲惫瞬间的记忆里,带着戈壁特有的、粗粝的温柔。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他们会看着,喉结上下滚动,咽下满嘴的沙尘气。(高帅)
审核:王峰 郭江涛 石贵明
校对: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