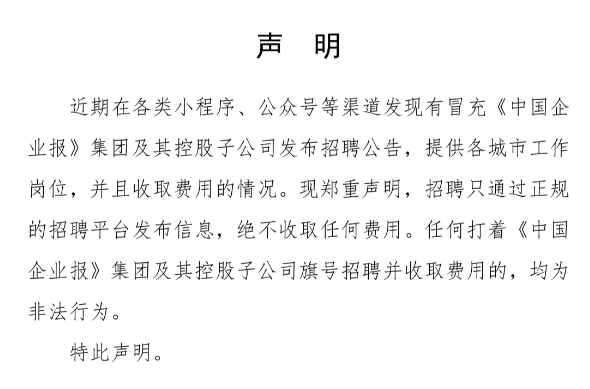清晨五点三十分,额济纳的天空还沉浸在靛蓝色的梦境中。我推开司机室的窗户,凛冽的西北风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像无数细小的针尖刺在脸上。远处,几株胡杨的轮廓在晨曦中若隐若现,它们扭曲的枝干如同被时间冻结的舞蹈。这是我在中铁电化运管公司呼和公司额济纳运营维管段担任火车司机的第五个年头,驾驶着货运列车往返于额济纳与马鬃山之间,累计里程已可绕地球赤道三圈半。每当有人问我为何从一个广袤草原"跳槽"到这片"生命禁区",我总是想起第一天报到时王段长说的话:"小伙子,记住,这里只有荒凉的地方,没有荒凉的人生。"这句话,连同那些铁轨边的胡杨,成为我在这片戈壁滩上最深刻的生命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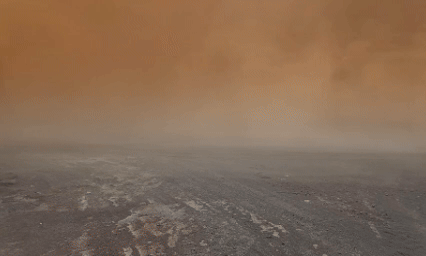
最初的日子比预想的更为艰难。三百五十公里的单程线路上,有三百二十公里是无人区。车窗外一成不变的灰色戈壁会产生诡异的催眠效果,我必须每隔十分钟就用湿毛巾擦脸。夏季驾驶室内温度高达50℃,汗水在座椅上洇出盐渍;冬季则骤降至-30℃,呵气在挡风玻璃上结出冰花。最难忘的是首次遭遇沙尘暴,狂风卷起的碎石砸得车体噼啪作响,能见度归零,我紧握闸把的手心沁出冷汗,突然在混沌中看见一株胡杨的剪影——它被风吹得几乎贴地,却始终未断。那一刻我理解了王段长的话:在这片土地上,连植物都在诠释着生存的尊严。

孤独会重塑人对时间的感知。在单调的柴油机轰鸣声中,我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计时方式:以胡杨为里程碑,以货运列车的车厢数为计数单位。运煤专列通常有五十二节,每节车皮长三十三米,整列车宛如移动的钢铁长城;集装箱专列像彩色积木,偶尔出现的冷链车会让我想象东海之滨的海鲜味道。漫长的驾驶时光里,我学会了用三十四种方法系工作服的纽扣,能背出沿线所有信号机编号,甚至通过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判断列车载重。这些无用的技能,如同胡杨树上多余的枝桠,是生命在贫瘠中对自身的丰富。

额济纳的星空下,我经历过最深刻的存在主义思考。某次上班因发现前方线路道床冲空停车十三小时,我躺在机车司机室,银河像倾倒的钻石囊袋悬在头顶。没有光污染的戈壁滩上,星星密集得令人窒息,北斗七星的勺柄几乎要碰到地平线上的胡杨梢头。在这种时刻,人会产生奇妙的渺小感与宏大感:渺小如沙粒,却又因与这片土地的联结而获得某种永恒性。我想起读过的一首诗:"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万物都在认真生活/蚂蚁搬运着巨大的死亡/胡杨记录着风的形状"。
五年间,我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隐秘丰饶。K712 桥下有一条河,每年五月会有成群的白鹭停留;川地拖站内的沙丘背面,藏着几丛开紫色花的沙冬青。这些细微之美需要以胡杨般的耐心去发现,它们教会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荒凉——不是匮乏,而是留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的手机相册从最初的自拍变成了胡杨的成长档案,最近开始记录沿线出现的野黄羊群。这种转变或许印证了生态学家所说的:当人长期凝视荒野,荒野也会凝视人,并在人心中开垦出新的疆域。
回望这五年,额济纳给予我的远比索取的多。它教会我在极限环境中保持尊严,在孤独里发现丰盛,在看似单调中捕捉无限可能。每当列车驶过那片胡杨林,我都会鸣笛致意,汽笛声在戈壁上空久久回荡。这些树知道,在它们注视下,有多少荒凉被锻造成闪光的人生。而我也终于懂得,真正的丰饶不在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而在于心灵对生活的开垦深度——就像胡杨,在最贫瘠的土壤里,活出最磅礴的生命气象。

在这片戈壁上,我与胡杨共同坚守,见证着时光流转。它们以不屈的姿态扎根荒漠,正如我将青春与热血融入钢铁轨道。胡杨精神“忠诚坚韧、守信自强、奉献担当,精彩永恒”的十六字箴言,早已刻入我的生命,化作永恒的信念,支撑着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在荒芜的天地间铸就不朽的丰碑 。(高帅)
审核:王峰 郭江涛 石贵明
校对:小强